撰文:帕特里克·贝尔福
翻译:栾力夫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是三百年的强盛加上三百年的衰落的故事。它是一个世界性大帝国、世界的十字路口。如果它保持优势,当今世界也会因此不同。但是,戏剧性的近代史却把土耳其挤出了强国之列,令它成为现代化和西方崛起的趋势中的一个被抛下、被欺凌的例子。在土耳其的跌宕国运中,中国读者能找得到祖国的影子,也找得到很多国际现状的根源。那段帝国时代是欧亚两洲,乃至整个世界近代不可磨灭、无法回避的历史记忆。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8年10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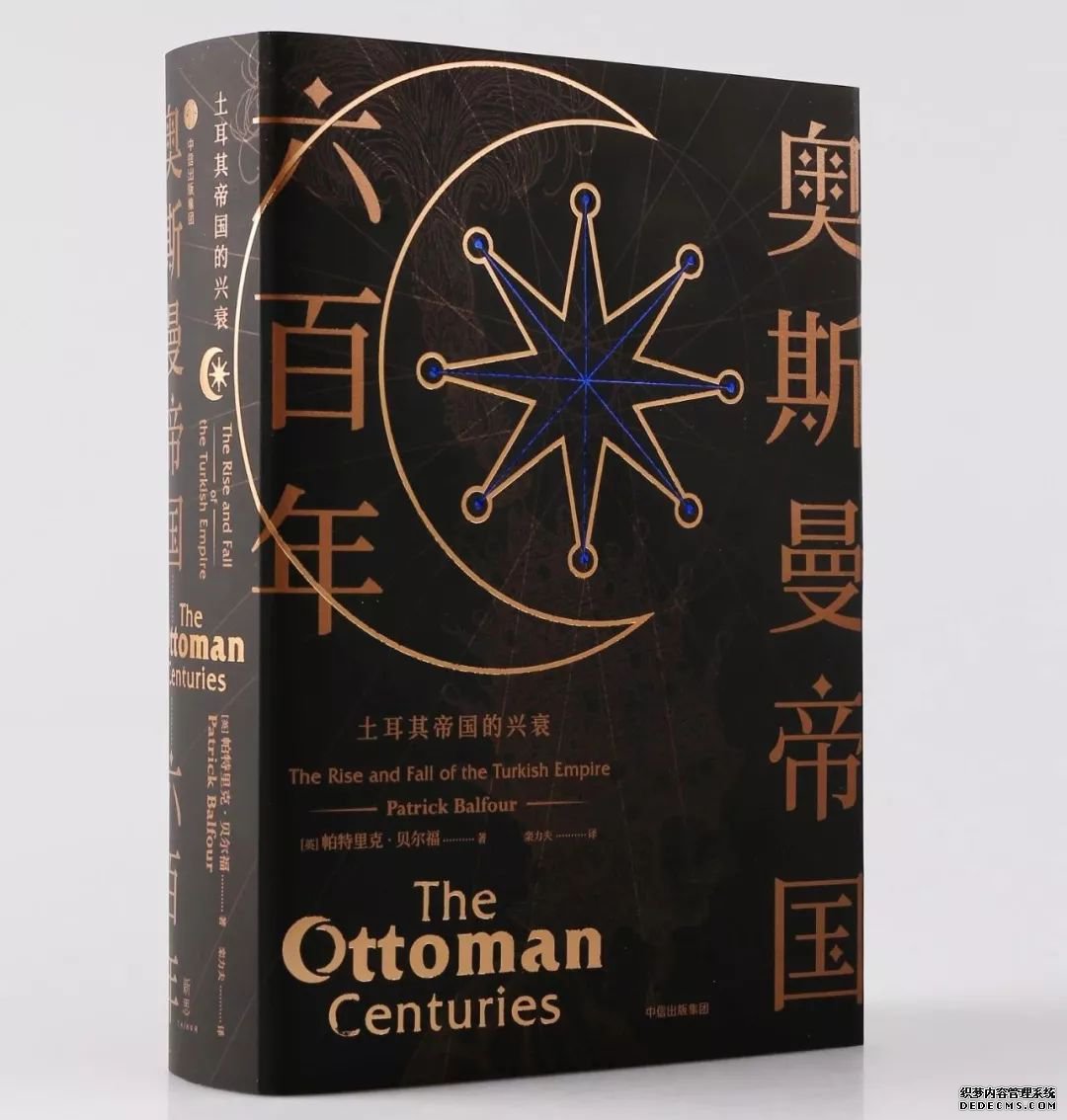
1
年轻的塞利姆三世于1789年继承了苏丹的大位,那一年也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年头。在俄土战争结束后,塞利姆三世以一个积极进取、全心全意的改革者的形象出现在国人面前,决心把半个世纪前的郁金香时期以来浅尝辄止的改革理念推行到实处。法国大革命也为传播这些改革理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起初,法国大革命仅仅被当作一个会影响到欧洲内部的事件。但是,少数有识之士很快就意识到,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一场新的思想运动,它不仅会影响西方,也将波及东方。与在基督教欧洲推动了种种进步的文艺复兴运动不同,法国大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与基督教分道扬镳、非宗教的乃至带有反基督教色彩的社会剧变。它是一场世俗主义的运动。因此,西方世界从法国大革命中汲取的养分,同样可以适用于伊斯兰世界,而不一定会与伊斯兰世界本身的宗教信仰和传统发生抵触。
塞利姆登上宝座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已经处于衰落之中,但是仍然保有它的大部分领土(只丢掉了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克里米亚和亚速)。不过,奥斯曼帝国已经长期陷于停滞之中,而且开始由于内部的分裂而出现崩溃的迹象。地方上强势的帕夏们经常藐视苏丹的中央权威,滥用他们生杀予夺和征税的权力;事实上,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大多都会滥用权力。不仅如此,许多省份都陷于叛乱之中,或是有发生叛乱的风险——从阿拉伯沙漠中强大的瓦哈比派(Wahhabites),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山区里的德鲁兹派教徒、伊庇鲁斯和希腊北部的苏利奥人(Suliot) ,再到一直藐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埃及马木留克贝伊们,以及被激起了独立精神的形形色色的基督徒族群。

塞利姆三世
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内部肆虐的还有另外一些具有破坏性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在封建制的基督教欧洲存在已久:在苏莱曼的时代还不存在、后来却不停发展壮大的世袭体系,成为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世袭封地的所有者数量也在迅速增长。这些地方上的小贵族被人称作“代雷贝伊”(derebeys),意为“谷地的领主”。他们手握权力和土地,藐视君主,欺压属民。农民和普通居民的生活普遍贫苦,而中央政府也面临着紧迫而难以化解的财政问题。为了应对这种困境,塞利姆需要在奥斯曼传统体制的框架之内,尽可能地实施效法西方式的改革,至少要在中央层面推行改革。至于奥斯曼的传统体制本身何时会变成对改革的阻碍因素、需要得到现代化改造,还有待观察。
在完成了与俄罗斯的和谈之后,塞利姆的改革就开始了。他的改革方案被统称为“新秩序”(Nizam-i-Jedid)。这一名称来自大革命之后法国建立的新秩序。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写给苏丹的信中提到了这个词语,引起了苏丹的兴趣。在筹备改革方案时,塞利姆前所未有地采取了集体磋商的原则。
1791年,正当远在多瑙河的军队刚刚踏上归途之时,他就已经向22位政、军、宗教界的要人(包括两名基督徒官员)发布指示,要求他们提交类似1789年法国人提交的“陈情书”(cahiers) 的“备忘录”。随后,他前所未有地成立了一系列商讨国事的会议和委员会,自由地讨论这些备忘录的内容。他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制订了“新秩序”的规划,其涵盖的范围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改革尝试。它不仅涉及军事改革,还涉及民政改革;他还计划制订一个总体方案,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并取得人们的一致同意;在这个规划中,复兴经济是一个高度优先的目标。
但是,最紧迫的需求还是进行军事改革。在派人去欧洲搜集政府、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的信息的同时,苏丹还特别派了两名代表去搜集军事方面的第一手信息。1792年,他收到了一份有关欧洲国家、特别是奥地利帝国的军事体系的详细报告。不过,在为新组建的军队提供训练和指导方面,他主要依赖的是法国人。他把自己需要的军官和技术人员的职位清单发到了巴黎——在早期的职位申请者中,还有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
奥斯曼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征求他们的意见:火炮(塞利姆对火炮尤为感兴趣,在登基之前还写过有关火炮的论文)、武器装备,以及改进铸炮厂和兵工厂的方法。早年建成的工程学校得到了大规模扩建。他们还建设了新的军事学校和海军学校,研习炮术、工事修筑、航海和各种辅助科目。教官大部分都是法国军官。为了方便教学,他们在苏丹的支持和鼓励下,兴办了一座大型的图书馆,收藏欧洲书籍。藏书大部分是法文书,包括狄德罗(Diderot)的理性主义著作《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法语也成了所有学生的必修课。1795年,文化领域的改革更进一步,早年间在伊斯坦布尔创办的法国印刷厂得以恢复,并由法兰西国家印刷所的一位主管负责管理,员工也都是来自巴黎的法国印刷工。因此,在秉承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导师及读物资料的熏陶下,奥斯曼帝国中出现了一群卓有见地的新一代人才。
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地区的法国人社群持续不断地加强着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这一方面是出于一种传教士般的情怀,但主要还是为了确保法国可以在这一关键时期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支持。土耳其国内一群颇有影响力的法国人支持大革命,身上戴着革命的标志,还召开革命者会议,这些行为惹恼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外交官。1793年,两艘法国船只在萨拉基里奥角附近鸣放礼炮,公开庆祝法兰西共和国国旗的启用。除了法国国旗之外,这两艘船上还飘扬着奥斯曼帝国的旗帜、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其他一些没有在可耻的暴君同盟中玷污自己的国家的旗帜”。接着,他们在土耳其的土地上还庄严地栽种了一棵“自由之树” 。在法国人的不懈努力下,伊斯坦布尔的社会也出现了变化。原本,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和西欧人之间泾渭分明,现在则出现了彼此关系十分密切的讲土耳其语的法国人和讲法语的土耳其人。他们会交流当前的需求和思想,一小部分具有影响力的土耳其人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热情的感染,开始向西方寻求建议和启迪。

